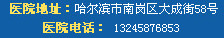刘俊吉:莒县东莞人,曾担任跋山水库工程指挥部政冶处副处长,第四师师长、水利基建师政委。城关镇党委副书记、书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人大副主任。
转战跋山
年11月28日,经过近2万民工一年时间的奋战,蓄水1亿立方的沙沟水库胜利竣工。
沙沟水库完工了,工地上的干部和民工到哪里去呢?工地党委领导传达了县委的决定:人不下马,马不停蹄,原班人马,搬到跋山。对于县委这个决定,绝大多数干部和民工都是心中有数也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在半月之前的11月11日,更大规模的腰斩沂河水利枢纽工程跋山水库已经开工了。跋山水库的蓄水量是沙沟水库5倍,工程量是沙沟水库3倍,预计需要民工5万至6万人,而当时尚缺额3万余人。沙沟水库民工移师跋山是必需的,何况沙沟水库的民工已经有了修建大型水库的经验呢。也不否认,民工经过一年的征战,远离家庭,舍家撇业,现在又到了寒冷的冬季,非常盼望回家团聚,这也是实情。工地党委召开团、营、连三级干部会,传达上级指示,进行思想动员,然后由各级干部再传达到全体民工中去。由于动员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加上是整体转移,不存在有走的有留的,工作也比较好做。更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个年代人的思想比较单纯,比较统一,服从领导的意识较强。领导一声令下,近2万名施工大军随带劳动工具、铺盖行李、锅碗霖盆,浩浩荡荡,当天就搬到了跋山。
我们政工科是随着指挥部一起走的。沙沟水库指挥部的成员,包括书记兼指挥黄国明、副书记徐传信、马元道,副指挥杜纪尧,办公室主任夏纪元都到了跋山水库。黄国明政委担任了跋山水库工地党委副书记兼工程指挥部副指挥,徐传信、马元道、杜纪尧、夏纪元分别担任师政委、师长、副师长等职务。我被公布为跋山水库政治处副处长,同时公布副处长的还有崔砚田、武逢春等,处长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宏吉,但是他还兼顾着组织部的工作,无法全靠在跋山,领导决定由我主持政治处的工作。
艰难的清基——崔家峪水利团的深水作业突击队
担任师长
年11月底,跋山水库工地已调集民工人,在指挥部以下编制有4个师、27个团、个营、个连。仅从人数和编制上看,跋山水库的摊子是够大的了。我当兵时在华野二纵四师十二团的一个连队当战士,知道一个师有上万人马,现在竟然有4个师,而且都集中在纵横10余华里的地域上,虽然不是用枪炮作战,而是用铁掀铁嵌和手推车筑大坝,场面之大,气氛之热烈,任务之艰巨,同战争年代打仗有很多相似之处。
大约在这一年的阳历年之前,王德臣书记找我谈话,说四师师长王维刚同志另有工作任务,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让我到四师担任师长。我服从组织分配,但提出缺乏工作经验,担心完不成工作任务。王书记只是鼓励我大胆去干,又简单介绍了一下四师所辖六个团的大体情况,我就走马上任了。四师辖城关、十里、四十里、黄山、高桥、马站六个团,有民工人。师政治委员邱文彬是个老同志,建国后不久就担任县农委副书记,后任柴山区委书记,年区改乡,乡又改称公社,他仍是柴山公社党委书记,年10月因兴建跋山水库撤销柴山公社,邱文彬接着参加了跋山水库工程建设。邱政委具备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一代领导干部的优点,对革命工作忠诚勤勉,党性强,讲原则,善于团结干部,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位称职的党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在与他共事的五个多月中,对我各方面帮助很大。
在参加水利工程建设前,我只是县委宣传部的普通干事,没有做过主管领导工作,加上年纪轻、阅历浅,一下子走到师长领导岗位,领导着l万人的民工队伍,发愁情绪是不可避免的。换个角度看,我经过沙沟水库一年时间的锻炼,天天在施工现场跑,天天与水库的进度、工效、典型事例和先进人物打交道,也逐步熟悉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运行规律和工作重点,加上我工作敢于负责,面对困难不屈服,也有决心有信心有办法把重担挑起来。
四师与其他三个师相比,有一个区别那就是所属六个团全都是原沂水县所辖的区、乡,没有从沂南县合并过来的团,我与所属团的领导干部全都认识,工作起来自然方便。那六个团的政委,全是原公社党委副书记,团长也是从乡长、副乡长(那时中央有文件,乡与公社合为一体,叫乡社合一,乡长副乡长同时也是社长副社长。但在习惯上仍称乡长副乡长,很少有称社长副社长的)中产生的。副政委、副团长的人选稍复杂一些,既有乡级、副乡级干部,也有一般脱产干部,甚至也有不脱产的管理区一级干部。
师、团两级都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民工习惯称“师部”“团部”,其实也就是晋通的几间棚子,除了睡觉的地铺行李外,连一张桌子、一部电话都没有。师部的人员除了政委、师长、副师长外,还有负责施工、后勤和宣传的几名科长,另外还有一名文书,也就是五六个人吧。每天除了留下一个人值班外,都分散下到各团各营连去,与民工同劳动,边劳动边指挥。当时施工实行“三班六倒”,昼夜24小时不停工。为了在现场实施坚强有力的领导,我与邱政委白黑两班跟班作业。邱政委年龄比我大十余岁,身体条件也比我差。我主动提出他跟白班,我跟夜班。开始跟夜班不习惯,特别到了下半夜,又困又乏,一蹲下就能睡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咬牙硬挺着,有时帮着上土,有时帮着拉车,看到有的民工疲劳时,我也替着推车子,仗着自己的体格好,身板强壮,边干边指挥能把民工带起来。
用瓢舀手捧等方法清理岩石空隙的积水淤泥
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提高工效
提高工效是一切工程施工的核心和关键,跋山水库建设工程受汛期制约,必须在年汛期到来之前完成筑坝任务(包括护坡)和输水隧道开挖浇铸任务。为了按期或提前完成任务,指挥部将总工程量按时间顺序分解到每个月、每10天、每1天,再将月、旬、天工程量分解到27个民工团,指标、定额都定得很死很紧,要求各个团必须完成每天的工程量,白天完不成晚上必须加班完成,不能拖到第二天。为了促进工效,工地党委和指挥部大力开展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挑应战,打擂台,评先进,插红旗,拔白旗,不仅高音喇叭表扬先进,批评后进,而且还在大坝阳坡显眼处一溜竖起了25根竹竿,每根竹竿挂着一面旗,旗上写着民工团的名字,根据前一天的工效排高低,一天一排,有很强的刺激性和鼓动性。像杨庄团始终名列前茅,他们的红旗高高挂在第一根竹杆的最高处,非常显眼。有几个团工效上不去,排名靠后,旗也挂得矮。四师的几个团工效也不平衡,相比而言,十里团、城关团好一些,经常排名上游之列,其他几个团的工效不理想,处于中下游状态。工效搞不上去,是最大的压力,不用领导批评,只要看一看旗杆上的红旗,自己就觉得脸上无光。我与邱文彬政委认真进行分析原因,也到杨庄团参观学习找差距,终于发现症结所在,根子还是出在干部队伍身上,归结起来有五条:思想作风不适应,模范作用差,树立典型不突出,生活没有搞好,宣传鼓动没有跟上。
师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统一思想认识,下决心克服薄弱环节,针对各团存在的问题,从实际出发解决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首先解决干部思想作风仍然停留在小农经济、生产队小规模生产、自由散漫、迁就照顾,掰不开面子的状态,在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上不会管队伍,不会带队伍,实际上成为群众的尾巴。在讨论中,有的在莱芜战役、孟良固战役、淮海战役中带过民夫的团、营一级领导,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修水库按军事编制,大兵团作战,思想必须跟上形势,就像战场上送弹药,运送伤员那样,行动战斗化,服从命令听指挥才行。接着讨论解决干部模范作用差的问题,当时正值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提倡思想整风和大辩论,对个别思想落后,精神不振作的干部开展思想帮助和批判,现在看有些过“左”,但在当时还是很有作用的。有的团领导怕吃苦,图享受,不能跟班作业,有的对安排当副职不满意,工作消极,甚至私下批准民工回家。按照工地党委的要求对这样的同志开展了面对面的批评教育,起到了教育本人、警示大家的作用。
在整顿干部思想作风中,我们注意从实际出发,既严格要求干部,又设身处地关心爱护干部。十里团和高桥团的政委因年龄偏大,身体又不好,我们与这两个公社党委书记联系,及时调整干部进行轮换。十里团新任政委是公社团委书记许洪烈,责任心强,办法多,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为了使水库前线的工作取得后方党委的支持,我们师每隔一段时间用写信的形式与六个公社党委进行通气联系,以便使党委及时了解情况,进行支援。
抓典型是提高工效的有效措施。工地上几个先进团有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有一个或几个典型连队或先进个人。如杨庄团有火箭连,王庄团有百虎将连,张庄团有猛虎连。我们四师的十里团工效比较高,也是因为这个团有一个刘胡兰队和模范队长郭淑菊。在刘胡兰队和郭淑菊的带动下,全团你争我赶,完成工效远远超过其他的几个团。我让十里团政委介绍培养树立先进典型的做法和经验,很快在全师所有团中都有了先进典型,比较突出的是城关团,他们挑选骨干组建了一个火箭营,营长由模范女青年赵发兰担任,教导员是管理区青年团书记张在田,他(她)们二人齐心合力,把这个营带动起来了,生龙活虎,工效超过省规定的定额一倍以上,而且把全团的工效也带动上去了,至年4月11日提前10天就完成了筑坝任务。四十里团也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记得其中有一个青年民工叫欧玉志,可能是欧家庄人,在各项施工中勇打头阵,表现突出。在清基回填的关键时刻,他肩扛粪篓下水填土,而且是来回小跑着,别人扛二趟,他能扛三趟。
在这期间,四师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得到加强。我在沙沟水库以及刚到跋山水库一段时间都是负责政治工作的,又有县委宣传部工作经历,对抓宣传工作不生疏。我召集师团分工抓宣传工作的同志开会,研究改进工地宣传工作的办法。很快就有了变化,师、团都有了宣传棚,形形色色的宣传鼓动口号,挑战书、应战书、决心书,表扬好人好事大字报等琳琅满目。我们还从民工中抽调了几个有文艺、曲艺专长的人,巡回在工地表演,活跃气氛。记得把武家洼京剧演员武明珂、高桥民间魔术艺人夏西行都抽调上来了。武明珂穿上戏装,画上脸谱,挂上大胡子,念念唱唱,很逗人乐。夏西行的戏法也很有趣,一会从耳朵里向外冒沙,一会空手抓出一盒“健美牌“香烟,随手把香烟扔给推车民工,或空手把一面小红旗插到推车上,有趣极了。
改进生活,提高伙食质量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军队基层有一句行话:“抓好生活等于半个指导员”,把这句话挪过来,就是“抓好伙食等于半个政委”。那时,县里给民工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天2斤毛粮。在那个年代,全国普遍缺粮的情况下,这个定量巳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水库施工是强体力劳动,施工者又是青壮年,这个定量是吃不饱的。为了解决吃饱问题,县委和公社党委想了很多办法,如由各公社和生产大队挖潜力支援,不能支援粮食,就支援副食如青菜、干菜等,由伙房食堂人员采集树叶、野菜,掺到慢头里。那时的主食是小米加地瓜干蒸干饭或卷子,面粉供应的很少,食用油也很少。我们组织伙食人员互相参观学习,研究怎样把饭做得多些,把卷子做得大些,尽量能吃到有油的菜。我又规定每个团分工一名副团长或副政委抓伙食。记得四十里团抓伙食的同志是供销社的干部,这个干部很有能耐,用各种办法使民工吃饱,保证了体力和工效。
老龙潭段回填现场
大战老龙潭
在50多年前修过跋山水库的那代人记忆中,恐怕没有哪一件事要比大战老龙谭印象更深。
老龙谭,是一个年轻而又富有想象力的名字,它地处大坝1+
—1+地段基槽负4-5米以下至基岩处,东西长度约60米,因这个地段在清基过程中涌水量大,给清基造成特别大的困难,而被施工人员形象的叫起的一个方位名。在未清基前,此处是沂河河床中央偏东部位,表层是黄白颜色的河沙,随着淌水缓缓流动,与其它地方没有什么区别。谁也不会料到,在它的底层竟潜伏着巨大的涌流。
老龙谭地段的清基让四师摊上了。凭我模糊记忆,主坝清基长度大约有米,每个师承担米左右,我们四师排在主坝东段。开始沿坝轴线向下开挖,清基比较顺利,当下挖到五米左右时,来自上游断面的渗水水量就多起来了,以至淹没了整个作业面,严重影响了继续下挖。这时,按照指挥部工程处提出的预案,在底槽一侧开凿导水沟,从导水沟将渗水引入积水池,由抽水机不停地将水抽出去,从而保证清基施工正常进行。这样向下挖了几米以后,在桩号1+向西约余米地段遇到大流量涌水,整个上游砂砾层渗水呈高压涌流状态,短时间内淹没了导水沟和积水池,淹没了底槽作业面,在几百米的距离上形成了一个带状水面,民工只能绾起裤子,站在冷水中掏沙,一掀下去只能掏出几捧沙,施工进度慢下来了。面对涌水的困难,指挥部一方面紧急向上级求援,迅速调集了几十部大口径抽水机,沿基槽安设了5个抽水站,昼夜不停地向外抽水。另一方面,号召民工发扬葛庄战役、盂良固战役我军攻坚顽强精神,吃大苦、耐大劳、战严寒,克服困难完成清基任务。同时改进施工方法,改造劳动工具,将直板掀改造为90钩子掀,用隔断横墙堵水、分段作业的方法,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使清基继续进行。
按照施工指挥部原来计划,要在“大雪”节气(年12月7日)前完成清基回填,西端和东端清基比较顺利,平均下挖10米左右到基岩,即开始回填。唯有老龙潭地段,由于遇到了出乎预料的特大潜流水,清基回填工期不得不向后拖了。指挥部主要领导荆守胜、王德臣、白廷杰、张培坤、黄国明等一天到晚川流不息地来到老龙潭清基现场,有时与团营连干部及技术人员开“诸葛亮会”,研究施工办法,有时拿起钩子掀把裤腿一绾跳进冷水中向外掏沙。为了尽量减轻冷水作业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专门安排后勤供给部门弄来了白酒,盛在桶里、缸里,下水前喝上几口以提高御寒力。同时弄来了一批深筒胶鞋和披肩雨衣,虽然达不到人手一件,但是体现了领导关心民工的一片心意。
年阳历12月7日是“大雪”,年1月21日是“大寒”,这是一年冬天最寒冷的一段时间。我们四师五个团(黄山团分工放水洞工程和其它工程,未参加清基)忘记了寒冷,全力投入老龙潭及以东地段清基,我和邱政委白黑跟班作业,什么星期天、节假日,冬闲(冬至)阳历年、元旦统统忘记了。这期间为了减少砂砾层渗水,曾经组织民工在沂河和暖阳河上游河床挖沟挖坑,想截住或减少地下潜流,但基本没有效果。“大寒”前后,地面封冻,河滩里、山头上都盖着白雪,老龙潭地段清基分秒必争,一尺一寸的向下延伸,两端完成清基的回填在慢慢向中间靠拢,米、80米、60米、50米、30米,大约快到阴历年的时候(这一年是小进年,除夕是阳历1月27日)就剩下最后的30米了,基槽深度也到了接近12米,有4层楼房那么高。巨蜇的潜流水仍威胁着清基,几十根抽水机管摆在槽底,隆隆的一个劲地向外扬水。十里团,城关团的青年民工,挤在槽底冷水中向外扬砂,一溜排在基槽斜坡上向外倒砂,冷水顺着掀滴落下来,浸湿了民工的头发,浸湿了他们的棉衣,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找不出什么安慰的语言。半夜时分,荆政委赶过来了,看到那感人的场面,感叹地说了一旬“:这真是个老龙窝呀!”我当时就站在荆政委身边,略加思索冒昧地说:“政委,咱不叫老龙窝,叫老龙潭不好吗?”荆政委毫不迟疑地说:“好,好!就叫老龙潭吧!”第二天,《工地快板》登出文章《英雄大战老龙潭》,自此,老龙潭这个名字就叫响了。
就在我们四师集中力蜇向老龙潭发起最后强攻时,一年一度的“年”节来到了。工地党委照顾到民工情绪,决定统一放假五天,但有些特殊施工任务不能停工,不能全放假,老龙潭的清基回填是不能停下来的,抽水排水也是不能停下来的。我们四师经过研究,决定留下足够劳动力继续施工,安排一部分年纪偏大的,有家口的民工回家过年。留下了多少民工现在记不清了,我和邱政委给留下来的民工讲话动员,说明不能回家的理由,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坚决拿下老龙潭,庆祝胜利过新年”。同时表态,我们师部的人团部的人一个也不回家过年,与同志们并肩战斗!实际上,不仅我们四师的师团领导干部没有回家过年,其他各个师、团的大部分领导干部也都没有回家过年,连工地党委和指挥部领导也是一样,在老龙潭施工现场的紧张劳动中度过了这一年的除夕和新的一年的大年初一。记得除夕那天,张清波副专员兼沂水县委代理第一书记与王德臣书记一同从县城来到工地,向施工民工提前拜年。荆政委几乎一夜未睡,坚持在老龙潭现场的劳动中与民工共度了这个有纪念意义的除夕夜。我的家在莒县东莞农村,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家里少粮缺柴,寒风冷舍,都盼着我回去过个年,可是我能回去吗,工程正在紧溜扣上,那么多民工都没回家,我连回家的念头都没有。
经过年除夕,年初一、初二连续三天紧张施工,到大年初二夜里,终于挖到老龙潭的硬底了,在13.5米深的基槽底部终于露出基岩来了,民工们用麻袋装土堵住上游渗水,当镐头和铁揪再也不能下挖,与岩石碰撞发出“当当“声时,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了,跳跃起来了!我下意识地抱起一块七、八十斤重的岩石,果断地下令:回填!刹那间,早已在基槽两侧斜坡上备好的几百方标准黏土,似塌方般地倾泄下来,一齐拥向老龙潭底部。为了防止回填土浸水稀化,我们指挥民工一刻不停地用脚踩踏,用石夯猛墩。不一会儿工夫,几百方黏土全墩上了,但上游断层的渗水仍在涌流着,如果不是抽水机排水,麻袋是堵不住的,只要渗水涌入回填面,那就前功尽弃了。在这危急关头,荆政委下达命令,调集人员,抓紧上土,随上随夯实,决不能让渗水浸过土面!其实我们几个团的民工已经做好上土准备了,几百辆推车不停地把黏土推来倒在斜坡上,再由工具向基槽深部输送。为了加快上土速度,民工们直接扛起抬筐,扛起粪篓,直接把土倒向土面。我在上面提到的十里团刘胡兰队队长郭淑菊、四十里团欧玉志以及城关团火箭营等,冲锋在前,勇打头阵,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
经过正月初二一整夜激战,老龙潭地段在50多米长的基槽上回填黏土三米左右,终于把老龙潭这个妖魔制服了,镇住了,压住了!天亮时分,我从老龙潭槽底走上来,被寒风一吹,禁不住打了一阵寒战,一阵晕弦,我赶紧蹲下来,觉得心慌,饥肠辘辘,实在有些撑不住了!老龙潭啊,老龙潭!你能有这个名字也有我一字改之功呢,你千百万年潜身沂河底层未曾出头,想不到一出头竟是这样狂荡不羁,桀赘不驯,以至搅得我们四师不能回家过年!我记准了,锁住蛟龙的时间是正月初二的晚上,现在已经是初三的早晨了,也是数万民工返回跋山工地的日子,这也算是我们师向兄弟师报捷喜讯吧。
老龙潭地段的填土迅速上升,到上土到5米左右时,履带拖拉机已能开上去辗压了。到了7米高程时,荆政委与我看了看现场,决定将上游导水沟撤掉,到此时才算是彻底降服了老龙潭。我是老龙潭清基回填施工的见证人,而且是现场负责的指挥员,我可以负责的声明,老龙潭清基是清到基岩了,我所以从基岩上抱出一块石头,就足以证明清基的质量。至于说是在岩层还有水的情况下回填也不太准确。当时上游断层渗水显确实很多很急,但我们采用了麻袋装土筑隔水导流沟的办法,将大流显渗流水基本控制住了,至于在回填土时的基岩上有水是事实,但都是比较浅薄的表层水,尽管用麻袋、干布擦沾,也很难阻断小流蜇渗水,在这种情况下,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大方蜇黏土回填,是能够筑牢坝心墙的。跋山水库竣工以来的50余年。历经多次特大洪汛,风浪考验,大坝黏土心墙包括老龙潭段位均安然尤恙,未发生严重质蜇问题,事实证明当年的施工质量是靠得住的。
服务部门送白酒到工地
竣工前后
进入年2月份,老龙潭地段回填迅速升高,只用了三天时间就与两端回填面拉平,完成了主坝清基回填任务。
这个月中旬,中央和山东省分别派出慰问团到跋山水库慰问民工。省慰问团团长是省文联副主席刘知侠,他带着从济南赶来的文艺界人士,白天到工地参加劳动,晚上在工地进行文艺演出,有京剧、吕剧、曲艺、杂技、魔术等,极大地活跃了民工情绪。刘知侠还亲自写了一篇报道《旧战场,新战役》,登在2月份《大众日报》上。他还用照相机亲自给英模人物照相,其中郭淑菊的照片就是他照下来的。慰问团中还有画家,在工地上画了很多劳动场面画,也给一些英模人物画像。
这个月20日,工地党委召开党的骨干分子大会,荆政委代表工地党委在大会上提出一个响亮口号:日进八、十,争取三个五,大战四十天,压倒小西山,庆功大会在跋山前”,第一句话是指人均日完成土方量,第二句话是指全工地日完成上土、沙壳,护坡工程量,力争在3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根据工地党委的号召,各师各团层层进行思想发动,连续发起了几个战役,工效有了明显上升。3月4日,大坝升到.55米(指海拔高度,下同)。3月21日升至.63米,3月30日升至.72米,3月14日打通输水洞。3月31日,杨庄团率先完成筑坝任务,我们四师十里团和城关团千4月11日完成筑坝任务,到4月20日,整个大坝高程达到.81米,4月18日,完成输水洞混凝土衬砌和明渠开挖,总工程蜇达到.35万立方米的跋山水库接近竣工了。
年3月3日,沂水县委根据工程进度,向省水利厅、地委及专区水利建设指挥部发出《关于跋山水库于四月初竣工进行拦洪的报告》,报告中称“根据现有4.4万民工劳动工效,预计再有20天左右,在3月底或4月初可以完成重要工程量,请求批准大坝合拢,确保本年蓄洪。3月26日,大坝西龙门合拢。4月1日大坝东龙门合拢。4月20日整个大坝完成合拢,各师分别召开总结会,5月1日召开竣工庆功大会。竣工大会会场设在大坝下游坡前怀里,用木棒木板搭建了一个简易主席台。主席台简单到什么程度呢,除了在前脸子上挂了一条“跋山枢纽工程建设竣工庆功大会会标外,台上摆了几张桌子、凳子,横着放了几排木棒当座位。那天气温好像比较冷,多数与会人员穿的还是棉衣。上主席台就坐人员,除了地委、专署、专区水利建设指挥部领导成员,沂水县委、县人委领导成员,工地党委和工程指挥部领导成员之外,民工师的主要领导和一部分先进模范人物代表也上了主席台,记得上主席台的人发了一个红绸布条,上写着“主席台“三个字。
不知由谁提议,我被推选为大会司仪。记得地委书记薛亭、副专员张清波(他同时还兼任沂水县委代理第一书记),副专员兼专区水利建设指挥部副指挥李肃,沂水县的党政领导张方庚、董文斌、王德法、王德臣、白廷杰、张培坤、黄国明等也都出席了竣工大会。地、县领导人都蹲坐在土台子上,和普通劳动者的穿戴没什么两样。
首先由薛亭书记代表地委讲话,然后张清波专员代表沂水县委讲话,王德臣书记代表工程指挥部讲话。深受民工和沂水人民爱戴,为跋山水库工程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荆守胜书记兼政委,因地委调他回费县参加紧急生活救灾,未出席竣工大会,成为所有与会者的遗憾。
究竟有多少民工参加了那天的竣工大会,现在恐怕难以查清了。在我模糊记忆中,有很大面积的一片民工坐在土坡上,应该不少于2-3万人。上面说了,从3月31日起,陆续有一些民工团完成了工程量,经过验收收尾之后,鉴于当时接近麦收,春种还没有完成,各个公社迫切需要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到竣工大会时大约有接近半数的民工已经返回家乡了。确切地说,参加竣工大会的民工是部分尚未回家的民工。
指挥部为全工地标兵团——杨庄团制作的红旗门
来源:沂水党史史志
原标题:《沂水百年党史丨担任修建跋山水库水利师师长的经历》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yf/4645.html